这两天,
很多人的朋友圈被同一个男人给刷屏了:
迪埃贝多·弗朗西斯·凯雷,
2022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得者,
也是获此殊荣的
首位非洲建筑师。

年近40岁才获得人生第一个建筑学高级学位,
此后在哈佛、耶鲁大学、慕尼黑大学任教,
曾获
阿迦汗建筑奖、谢林建筑奖等多项业内大奖,
设计的学校被《纽约时报》评选为“二战”后
全球最重要的25座建筑之一……
尽管他身上的光环让人膜拜,
获奖之前却很少有人听过他的名字。
而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为人一样,
谦逊、大胆、创新,充满力量。 关于泥土的“巫术” 1965年,凯雷出生在布基纳法索的甘多村。
这儿地处撒哈拉南面,
白天的最高温度可达45度,
雨季虽短,却来势汹汹。
不少人因为炎热、缺乏干净的饮用水、
疾病等原因悲惨死去。
连基本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, 更别提教育和建筑了。 
作为村长的儿子,凯雷是幸运的。
7岁那年,他带着“全村的希望”,
远走20公里去隔壁的滕科多戈上学,
成了镇上第一个识字的人。 当时的教室却可以用“煎熬”来形容——
水泥墙无法很好地散热,光也照不进来,
每天150多名同学挤在一起,
简直就像一个蒸笼!
“
我要建一所舒适的学校”,
从那时起,凯雷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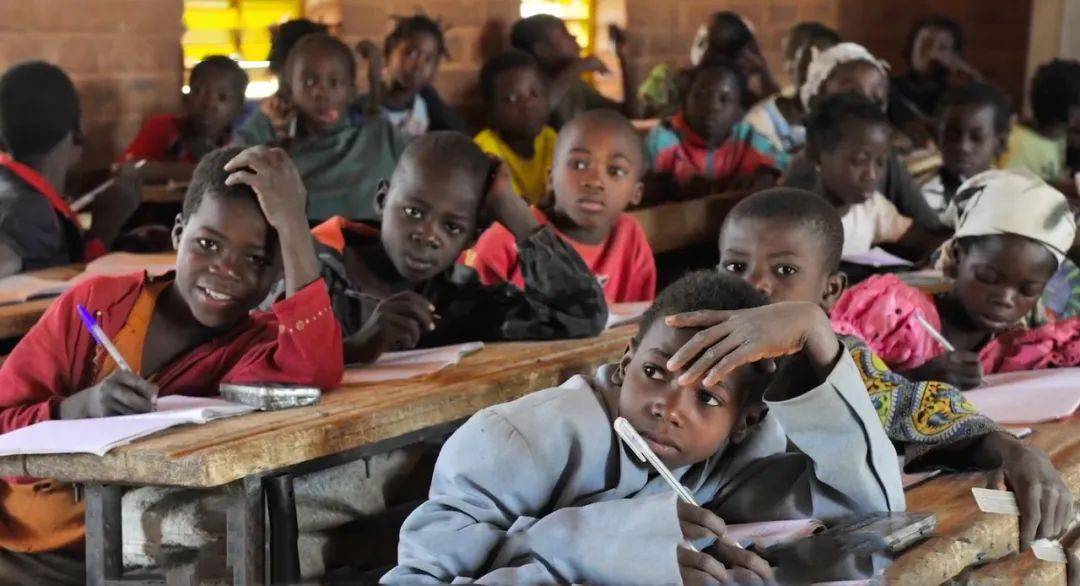
1995年进入柏林工业大学学建筑后,
凯雷便开始设计甘多小学的草图,
后来又辗转筹集到5万美元。
可当他把消息告诉村民的时候,
却受到了大家的嘲讽:
粘土房屋不可能经得住一整个雨季的折腾, 而凯雷竟然要用它建学校? 粘土这种材料祖祖辈辈们都在用, 这难道就是凯雷去欧洲学习的成果吗? 
▲改造粘土
凯雷自有他的想法——
粘土是最适合当地气候的,
只要对它加以改造,
不仅可以降低搭建成本,提高工作效率,
还能让大家对这种“穷人的材料”刮目相看。


▲改造粘土
他以粘土地面为例,
在里面混入了一定比例的水泥后,
让村民们轮流在上面捶打,加水,再捶打,
直到粘土变得像砖块一样结实。
最后再用石头给它抛光,
过上几个小时,
就和“跟婴儿的屁股一样光滑”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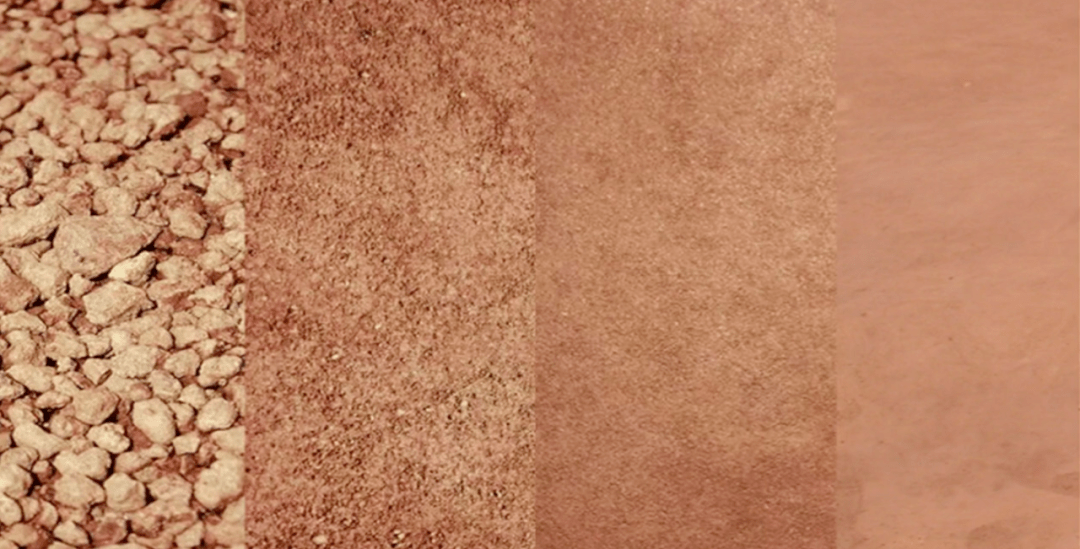
▲改造后的粘土
可是这到底能不能应对降水呢?
凯雷用了各种办法和村民们解释。
比如制作完一块砖后,
在它中心放一桶水,
5天之后拿出来依旧是固体。
同时,因为大雨冲刷后,
河流里的砂块和碎石正好是建筑所需,
用它应对雨季毫无压力。

为了进一步证明粘土的承重能力,
凯雷还用它建了一个拱形,
然后和团队“嗖”地一下跳上去,
艾玛,模型依然坚挺!
就这样,凭借着
耐水、坚固、可持续使用, 改良后的粘土成了建造的主要材料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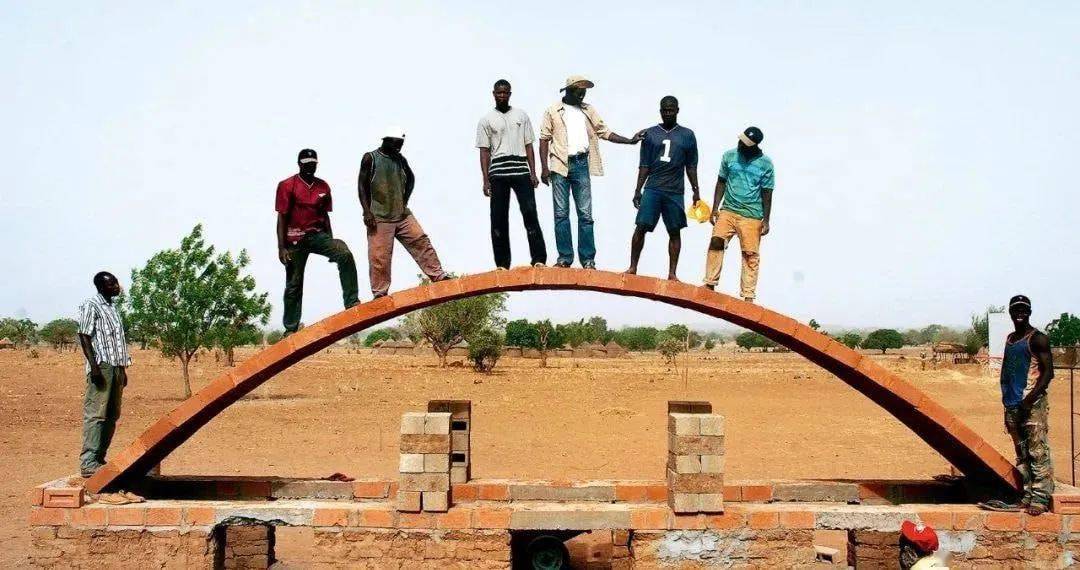 接下来着重解决散热的问题。
接下来着重解决散热的问题。 除了粘土砖自身可以很好地散热之外,
凯雷还在教室上方支起了悬空屋顶,
中间用天花板隔开并设置好开口,
根据“冷气下沉,暖气上升”的原理,
空气可以自由地“上蹿下跳”。


有时,凯雷还会通过放置水平窗户,
形成更完善的“
被动通风系统”。
虽然这样不能改变太大的温差,
但有风吹进来已经足够让孩子们兴奋好久啦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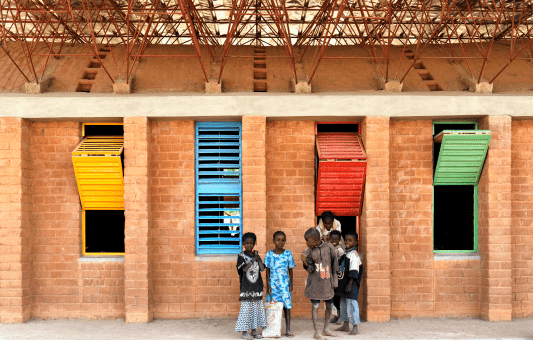 “在布基纳法索,好的建筑就是一间教室,你可以坐在那里,让滤过的光线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入,照在黑板上,或洒在课桌上。
“在布基纳法索,好的建筑就是一间教室,你可以坐在那里,让滤过的光线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入,照在黑板上,或洒在课桌上。 经过所有村民的努力,
甘多小学终于在2001年建造完成。
在读学生人数也从120名增加到了700名。
2004年,甘多小学被授予阿迦汗建筑奖,
也为更多项目的开展创造了机会。

▲甘多小学
在建造
甘多小学图书馆时,
凯雷采用了一项技术创新。
看到这一个个陶罐没有?
凯雷把它们切成两半后插入了天花板,
当阳光从这“蜂巢”一样的洞口透进来,
竟有种浪漫的光影效果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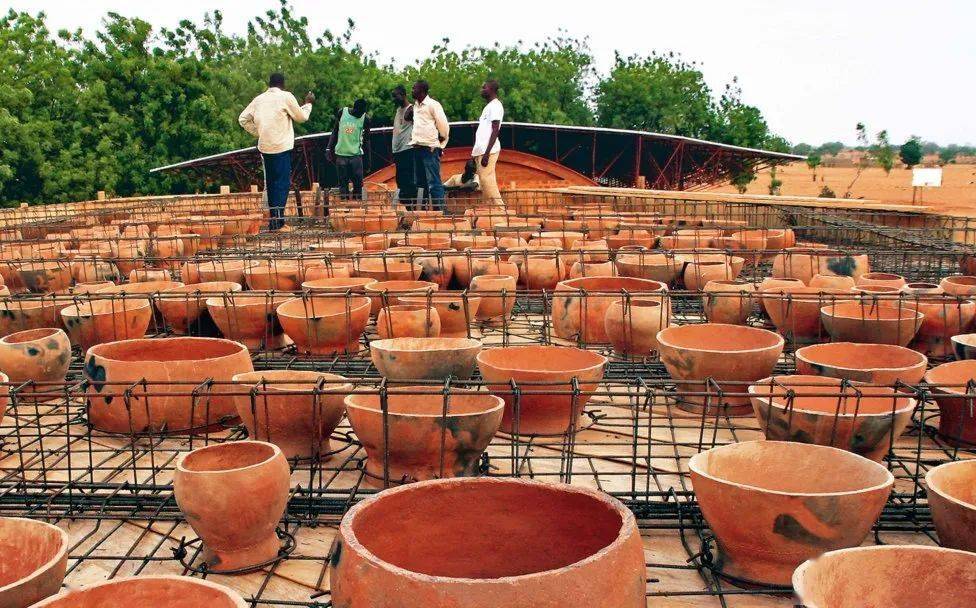

▲甘多小学图书馆
这个设计还延伸到了后来的
本加河畔学校。
凯雷把木百叶和陶罐做成更大的开口,
又配上了额外的遮阳和防雨措施。
这下,教室不仅更加敞亮了,
暴晒、暴雨,也都不在怕的!


▲本加河畔学校
Lycée Schorge中学的设计可能是最诗意的, 格栅墙的使用增添了几分自然的味道,
配合经典的悬挑屋顶和通风塔,
可以说是驱热的“黄金搭档”!
看书写字当然少不了光,
教室里的白色石膏天花板解决了这个难题,
通过漫反射原理可以获取充足的自然光照,
孩子再也不用担心熬坏眼睛了!


▲Lycée Schorge中学
狮子初创园区的灵感来源于白蚁群“建造”的土丘,
这高耸的通风塔看起来可不是一般的威风!
它能帮助冷热空气对流,
同时也和周边的坡地景观很好地融合在一起,
象君看了都想去打卡拍照!


▲狮子初创园区
自然通风、双层屋顶、切题的热交换能力、
高耸的通风塔和遮阳手法……
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,
凯雷坚持运用本土元素,
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建筑语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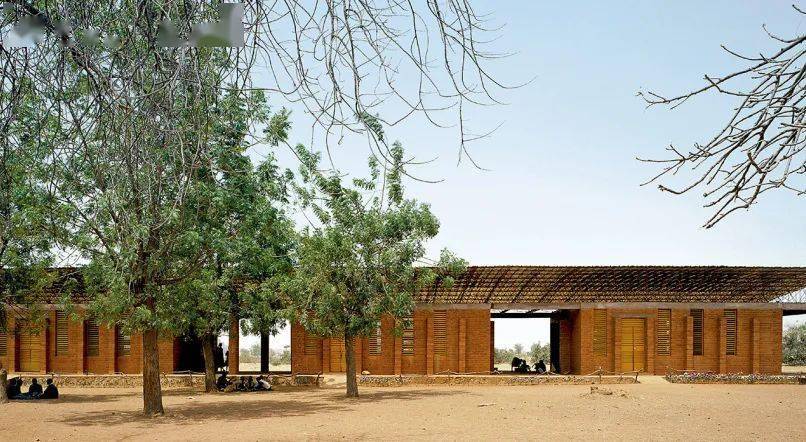 “我希望我的建筑能够启迪那些使用它的人,让他们感到快乐。”
“我希望我的建筑能够启迪那些使用它的人,让他们感到快乐。” 作为一名建筑师,
凯雷始终都没忘记过他的初心。
“穷可以,但不能安于现状” 凯雷在一个没有幼儿园的社区长大,
对当地人来说,社区就是一个大“家”。
“我记得我祖母坐在只有微弱灯光的房间里讲故事,而我们则紧紧挤在一起,房间里回荡着她的声音,也将我们包围在其中,她招呼我们靠得更近一些,形成一个安全的所在——这是我对建筑的第一次感知。” 
上学后,
凯雷每次返校前都会挨家挨户地去告别,
妇女们就会打开她们的口袋,
把身上仅有的一枚硬币给他。
母亲告诉他,
这枚硬币代表着大家对他的感情,
他们都希望他能学成归来,
帮助改善社区的生活。
从此,“社区”就像一根无形的线, 牵引着凯雷承担起更多的责任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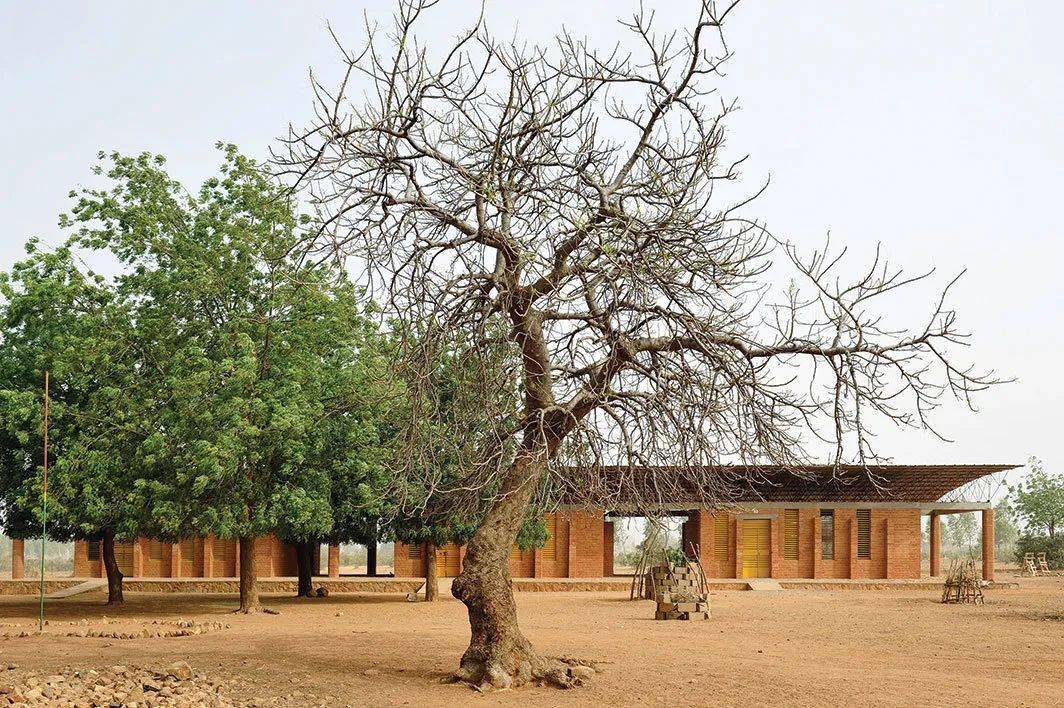
2001年,凯雷创立了Kéré基金,
除了用于筹集项目款项之外,
他还鼓励村民们都参与到建筑营造中来,
甘多小学便是他们共同完成的第一个建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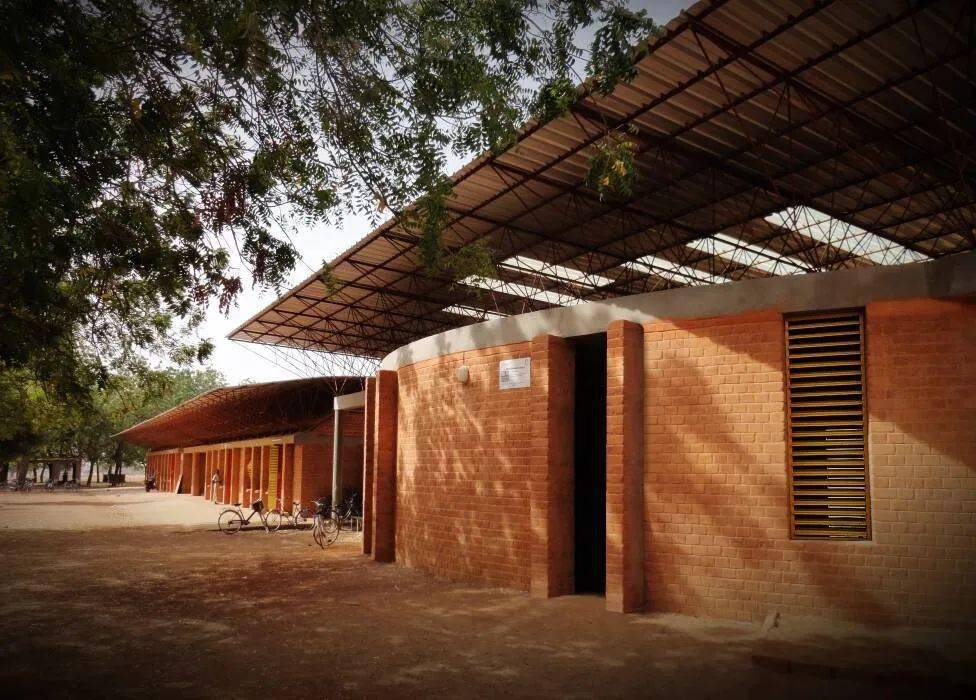
▲甘多小学
男的负责搭建,
女的给他们挑水,
孩子们到处收集石块……
社区的每个人都为搭建提供帮助,
也逐渐在不同的项目中掌握了不同的技能。

此后,每次一回到甘多,
凯雷都会向家乡父老传授有目标的想法、
技术知识、对环境的理解以及美学方案等。
村民们不用背井离乡也能赚钱养家,
这让他们充满了希望。

甘多小学建成后,
凯雷在德国柏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:
凯雷建筑师事务所。
他继续带领勤劳的甘多村民
一起建造了更多的美观、实用的建筑。
猜猜这些神秘的大盒子到底是啥?
其实,它们是新建的
教师宿舍,
不仅使用了粘土墙和土坯屋顶保持室内凉爽,
还人性化地使用了一人一户的“住宅”概念,
被大家誉为“奇妙的冰箱”。

▲教师宿舍
马里国家公园里绿荫环绕,
它与环境地形完美融合,
同时容纳了餐厅、体育场、售货亭等公共设施,
是个很好的休闲场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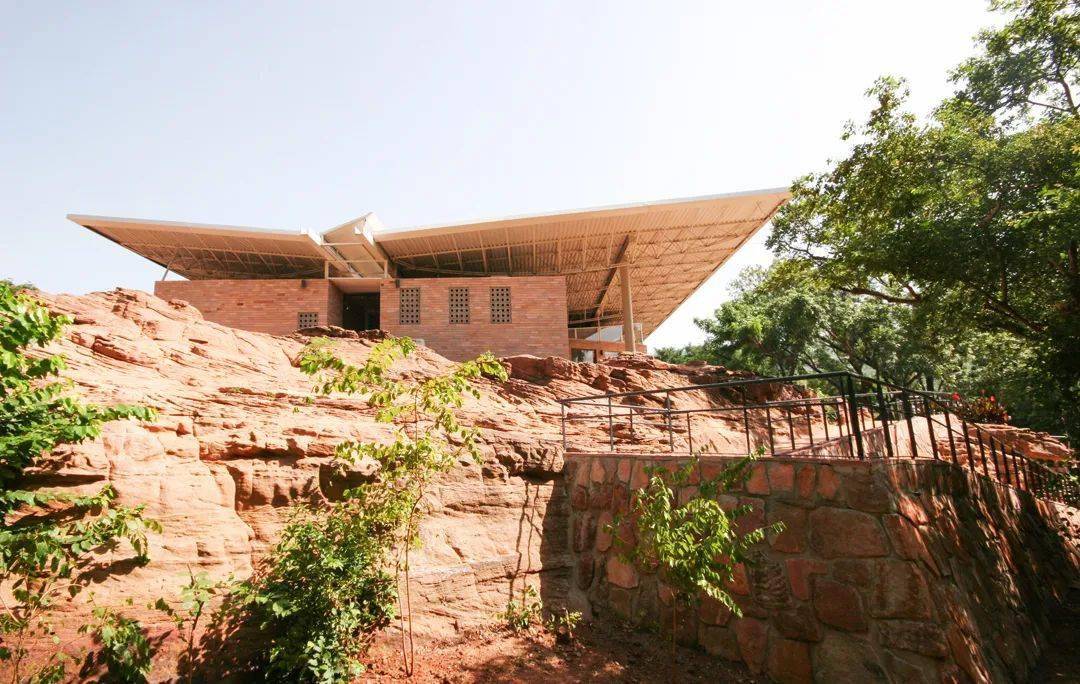

▲马里国家公园
歌剧村一定是艺术家的孵化地,
歌剧院、艺术家工作室、学校等在这里拔地而起,
毕竟,穷什么,也不能穷精神啊!


▲歌剧村
医疗与社会福利中心提供妇科、牙科和全科服务,
这高低错落的窗格真是十分友好,
每天醒来就能看到如画的风景,
病也能好得更快吧!


▲医疗与社会福利中心
“我希望他们开始梦想拥有更好的生活,而不是安于现状。” 通过建筑,
凯雷改变的不仅是人们的生活,
还有创造幸福的能力。
带着记忆,走出非洲 凯雷的设计之路不只是一个“回乡”的故事,
随着他在非洲的建筑作品
在邻国、欧洲、美国等掀起热潮,
凯雷也重新开始思考他的设计。
2017年,
凯雷受英国蛇形画廊邀请,
在伦敦的肯辛顿花园设计一座
展亭,
这是他设计生涯的高峰。


▲蛇形画廊展亭
他把展亭设计成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,
瞧这形态,就是相比周围环绕的真树也毫不逊色!
漏斗形状的“树冠”让人想起此前的悬挑屋顶,
用它收集的雨水可用来浇灌景观绿地。
嗐,喊了那么多“节约用水”的口号,
倒不如这个简单的设计来的实用!
更特别的是,
它的围墙是开放的,
用非洲文化中象征着力量的蓝色,
和非洲纺织物上的纹路增添了不少民族风情。
穿上草裙,打起非洲鼓,瞬间有内味儿了!


▲蛇形画廊展亭
与西方文化追求“独立”和“私人空间”不同,
“树”在非洲文化中寓意着“社区”间的感情和连结,
在树下聚会议事也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传统。
所以当这座开放的建筑出现在英国的花园里,
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就显得十分微妙。

▲蛇形画廊展亭
除了展亭的设计,
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主集会方式,
也被凯雷用在了
贝宁国民议会的设计构想中。
它坐落在一个公共公园里,
中空的“树干”承担起整座建筑的通风采光,
屋顶是一个荫庇众人的“树冠”,
前来集会的市民可以在此休息片刻,
然后沿着螺旋楼梯拾级而下,
就能抵达集会大厅参加议事。
还真是既不耽误纳凉,又不影响办事,
一举两得!
“真正创造一种各方都能积极参与的集会,这才是它本来民主、透明的样子。” 

▲贝宁国民议会
过去,受到西方殖民的影响,
非洲“被动地”卷入了现代化的浪潮,
却不曾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。
比起对西方文化盲目的“拿来主义”,
凯雷更加相信,
非洲的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知识。
所以,他在自己的设计实践中,
一次次追本溯源,回归故土之根,
也尝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对这些知识重新利用,
把它们推广到西方,乃至全世界。
 “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有能力去变革,而不是随大流。这是一种荣幸,也是最好的做事方式。”
“穿梭在两种文化之间让我有能力去变革,而不是随大流。这是一种荣幸,也是最好的做事方式。” 无论走出多远,
都别忘了来时的路。
这可能是凯雷除了建筑学以外,
教给我们最质朴的道理。
图片来源: 弗朗西斯·凯雷
资料参考:
三联生活周刊:《2022|普利兹克建筑奖,第一次颁给了非洲建筑师》
InsGirlADCNJobs:《弗朗西斯·凯雷的思考与实践,一文了解新晋普奖得主(专访+项目合集)》
良仓:《2022年建筑界“诺贝尔”奖颁给了一位带动“全民一起建小学”的非洲建筑师》
世界建筑:《WA丨2022普利兹克建筑奖揭晓:迪埃贝多·弗朗西斯·凯雷丨附主要作品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