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527801728 | 2021-08-04 07:52 |
|
每天一条独家原创视频 39岁的作家杨潇, 过去当过14年特稿记者, 采访过郎平、昂山素季, 报道过网戒中心、中国文物走私链、和汶川地震, 被行业内称为中国最好的特稿记者之一。 2018年他花41天, 以徒步为主,穿越1600公里,从长沙到昆明, 重走了当年西南联大“湘黔滇旅行团”的西迁之路。 还采访了9位旅行团的二代、三代。  他将一路上的见闻, 与80年前旅行团的故事交织在一起。 写成新书—— 《重走:在公路、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》, 有人评价其是当代的《西行漫记》。   西南联大称得上中国最牛大学, 旅行团中的不少成员, 在如今听来如雷贯耳, 但在当年他们不过是20岁左右的少年, 大多不曾见过中国的内陆。 他们日行40公里,睡猪圈, 一路提防匪徒,躲避虎豹, 却仍坚持采风、搜集民谣、勘探地质, 写出了第一本中国人自己的西南实录, 还鼓舞了当时抗战的决心。 他们面对动荡、战火时的焦灼与勇气, 让不少读者泪奔, “重走西南联大, 像是重新去抚摸一个国家的脊梁”。  我们在北京见到了杨潇, 跟他边走边谈。 “联大学子在路上, 梁思成、林徽因、丰子恺、沈从文也在路上, 它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, 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, 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。 我要像他们一样, 在路上,重新发现中国。” 自述 | 杨潇 编辑 | 陈星 责编 | 倪楚娇   重走,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2018年,我迎来了第三个本命年,却陷入了很深的迷茫。 我从前是一名记者,写了10多年特稿,后来做过时尚杂志副主编,也拍过长视频。36岁这一年,我发现这一切都已经不能满足我了。 我刚好读到一本书——《联大长征》。当年为了躲避战火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的学生被迫西迁,300名师生历时68天,徒步1600公里,最终到达昆明,与另外两路师生汇合,这才有了西南联大。 我读学生们的日记,看到他们被迫离开课堂,投入一段未知的旅程。我觉得这种状态和我很像。于是我决定和80年前的年轻人一起上路,找回自己的方向感。 2018年4月,我正式出发。   我准备了一个42升的登山包。 里面有一件冲锋衣、一条速干裤,两套贴身换洗衣物,防晒霜,干衣机,干鞋器,电脑,洗面奶,羽绒背心,用得只剩一点点的牙膏,一个强光手电筒和厚厚的一本《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——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》。 我试图弄清楚,他们一路上的日常生活什么样?所见所闻如何影响着他们?他们又如何处理国家与自我的危机?  每到一个地方,都会到地方档案馆找县志 在站点和旅行方式上,我尽量跟他们一一对应。 他们从长沙去益阳是坐船,现在没有船了,我就坐绿皮火车。他们从益阳开始徒步,我也从益阳开始徒步。 每天走20-30公里,早上10点出发。每到一个地方,就到方志办、史志办去看资料。然后沿着城市走两圈,打卡学生日记里提到的重要“景点”。 我不仅要在空间上重走一遍,也期待跨过时间与师生们相遇。 长沙的湘江景色   长沙临时大学旧貌 故事的起点:长沙临时大学 我一到长沙,就去找长沙临时大学的旧址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,三所高校最先是在长沙组成了临大,随后才西迁改名为西南联大。   圣经学院的过去和现在 当时学校租用的是韭菜园1号的圣经学院,如今成了湖南省人民政府机关二院。 男生宿舍现在已经找不到了,位置应该在湖南省人民体育场和展览馆之间。他们当时洗澡,不是在宿舍屋檐下便是在露天的院子里,一个个都是古灵精怪的人物。  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“停云楼”  如今的停云楼已经完全破败 文学院在南岳的停云楼,在这里“每人一木架床,一长漆桌,一椅,煤油灯。”闻一多听着风雨声一夜无眠,金岳霖、燕卜荪在阳台上谈论维特根斯坦。 如今,房子已经完全破败,屋顶都是茅草和藤蔓植物,玻璃窗全部荡然无存。 长沙出现空袭  开学后第三周,长沙出现了空袭,一天来了4架战机,死伤300余人。炮弹落在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临时住所只有十米的地方。大家皆往地下室躲避。长沙成了一个伤兵的世界。 临大不得不再度西迁。布告一出,学生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“去不去昆明”,变成了“是步行还是走海路”。 最后师生兵分三路前往昆明。 其中最艰苦的方式是徒步去昆明。这不是最经济便捷的方式,却是对抗战意志的极大鼓舞。另外两路需经过多个国家的殖民地。只有步行能实现,从中国到中国。 师生离开长沙不到9个月,长沙就在文夕大火中化为废墟。  湘黔滇旅行团的教师:李嘉言、李海峰、李继侗、 许伟橘、黄钰生、闻一多、曾昭抡、吴征镒、毛应斗 千里迢迢去昆明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近292名学生。在11位带队教师中,最有名的要数闻一多。 闻一多虽只有40来岁,但特别显老,看上去很不能走路。好友杨振声戏说:“一多加入旅行团,应该带一具棺材走。” 这个说法并不夸张,我在徒步的第二天就差点支撑不住。第一天明明可以负重走那么远,没想到休息后反倒直接崩盘。后来我一路上几次给背包减重,最后连肥皂都切成了两半。 特别有趣的是,旅行团似乎也在第二天崩盘了,按照计划他们每天应该7:00出发,但第二天一直推迟到了8:40才出发。  旅行团是按行军组织的,早上6:30起床,最晚8:00上路。这三百个人住哪里,安排多少个房间,借多少稻草来铺地,谁烧水,谁采购,谁做饭,一切都是有组织的。 黄钰生是管钱的。旅行团每人每日伙食费原本是2角,他将其提高到4角,经过的多为贫困地方,但是都会有养猪的,就可以买到猪肉。 “旅行团伙食班煮的红烧肉最享盛名,色香味俱佳,参加过旅行团的人大概都终身难忘……”其中随行的一名厨子,还是冯友兰家里的。河南的厨子,做面食特别好吃。  那时候打牌很流行,有的学生为了打牌,会走得特别快,先到了目的地就可以先打牌,一边打牌一边等人来,这方面是很自由散漫的。 那会儿的学生都喜欢合唱,唱歌是最好的激发士气的方式。 晚年接受采访的黄钰生回忆说,“我们一路上唱着游击队之歌、我们都是神枪手,还唱聂耳的歌。我们吃得很好,睡得不可能很好,有时牛舔我们的脖子,就在牛厩的旁边睡了。”  探寻80年前的旅行团足迹 安顺火牛洞是我重点打卡的“景点”。 当年为了利用回音丈量洞穴的大小,闻一多曾在此“高歌”过两曲,一首是经典的那不勒斯民谣《桑塔·露琪亚》,一首是当时在美国流行的《胡安妮塔》。 我读着这些记述,对火牛洞有着无限的向往。 现在的火牛洞,已经更名为“犀牛洞”,洞口有红色油漆铁门把手,门没上锁,洞口是碎石和木料。我举着手机电筒的光,向里面走了几步,又退回来,无数恐怖的画面在脑海中划过,最后放弃了进洞的想法。   鹅翅膀大桥的现在和过去 当年旅行团来到的“鹅翅膀大桥”,是保存完好、全国修建时间最早的公路立交桥,是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座里程碑。 我就是冲着这座桥去的,但最开始只看到一座平平无奇的水泥大桥,后来碰见一个开小货车的小哥,他告诉我:“我们管它叫螺丝桥,二战前就有了。” 我立刻兴奋起来,心不累了,腿不沉了,噔噔往下冲,对比80年前的照片,这应该就是真正的老立交桥。 当年闻一多在这里掏出了铅笔画了一张素描。“鹅翅膀”三个大字,已经破损大半。大部分青砖都有一层烟熏过的黑色,好像战火还停留在上面。   北盘江的现在和过去 旅行团抵达北盘江的时候赶上了急流,江面宽不过四十米,水是黄的,很急,有很多的漩涡。 河上原本有一铁索桥,历经明清两代,新桥建立后发生事故,师生不得不坐船渡江。以篙撑船,逆水而行,算是此次旅行中最惊险的一幕。 现在的北盘江水位已经上升了15米,基本上激流都没有了。  青溪 旅行团在青溪曾投宿的万寿宫  沿路上我最喜欢的是贵州省的青溪。一条马路横贯东西,家家门口都有一小块空地,户户有花,没有车来车往,也没有集市和摊贩。这儿的人也都特别友善。 不知当地人是否知道,在光绪年间,这里曾建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钢铁工厂,占地60亩,三个高大的烟囱,32件大型机械,全套在英国采购。但在1937年旅行团抵达时,这里只剩下三根烟囱。 铁厂、围墙、烟囱,历史就像一个大搅拌器,我们都只是在里头浮浮沉沉。  旅行团路途艰险,常遇雨后路滑  地点可能在镇远,也可能在关索岭 在路上认识中国 湘黔滇旅行团的许多人都试图在路上理解中国。 进入贵州,旅行团对鸦片印象深刻。有一个学生写道“恐怖的山谷,罂粟花,苗族的百姓和瘦弱的人们,使我觉得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”。 吴大昌告诉我,“江浙和平津都禁烟禁得厉害,但一进到贵州,路边你就能看到他躺在那里吸鸦片,就如路边晒太阳者一样常见。”  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是“多习民风,考察风土” 按照临大校方给学生的要求“多习民风,考察风土”,旅行团成立了摄影组、地质组、采风组,还有民间歌谣采集组,闻一多是歌谣采集的指导。 负责歌谣采集的是刘兆吉,因为西南方言不通,还有男女授受不亲之嫌,当地女性见到他们就跑掉了。 刘兆吉沿途上搜集的民谣,很原始很野蛮,歌词是“要想老婆快杀敌,东京姑娘更美丽”。他感到不适,但是闻一多却批评他,说他还是孔夫子的那一套。最后刘兆吉坚持了下来了,在1946年出了一本《西南采风录》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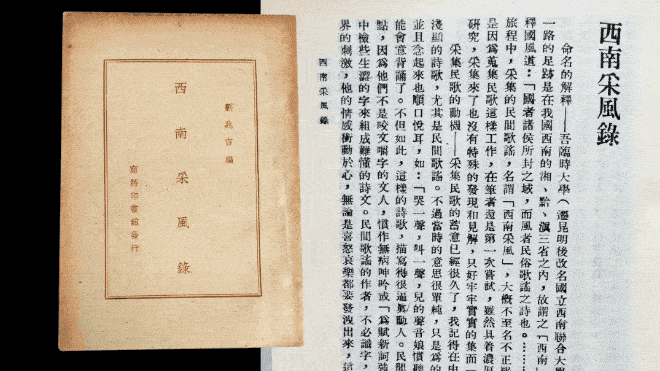 当时的大学生,出身都还不错,没有见过真正的贫穷。在旅途中他们看到,很多农户在春节过后就无粮可吃,孩子失学在家。同行的师生们还目睹了农村抓壮丁,被绳索捆绑而去。 有一个学生,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内地,在旅行团中第一次看到中国内地老百姓为了照明,只能点煤油灯,最后就去学了水利发电技术专业。 还有一个学生,在临行前看到中国西南地区的记录多是外国人做的,受到了刺激,后来他出版的《西南三千五百里》成为旅行团的第一本著作。 旅行团中途休息,在盘县附近  这段旅途,算是他们的一个成人礼。他们甚至用“Grand tour(壮游)”来形容自己。 我又想着自己的青年时代。我把那些时间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?我是不是在电视节目、体育比赛,或是手机上浪费太多时间了?是什么造成了我们与那两代人的巨大差距? 更多时候,我连这样问的雄心都不够。 旅行团到达昆明时受到热烈的迎接  老人是我最想感激的 沿路上遇到许多老人,我会挑眼睛有光的和他们攀谈。他们记忆力很好,你只要一张口,他们就能和你说上半天,依据他们的讲述,就能重建一个城市。 我专门去拜访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唯一还健在的成员——吴大昌。他是北理工的退休教授,今年已经103岁了。 吴大昌今年103岁了   吴大昌所在小队 我第一次去找他,足足聊了4个小时。他还记得查良铮(笔名穆旦)一边走路一边轻声念字典的样子,念完一张,撕一张,等走到昆明,字典都撕完了。 他还记得,一路上大家的脚都起了水泡,校医教大家把针烧红消毒,从水泡中间穿过去,再留点线头在水泡上,避免再起。“同学们互相帮忙,自己有时候下不了手啊!” 他说自己的人生是5年、5年过的,41岁的时候检查出膀胱癌,做了切除手术,从此5年为一个节点,就这样,他活到了80岁,90岁,100岁。今年年初我去见他,他更精神了。  我在中南大学的院士楼拜访了赵新那 她的父亲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 我还拜访了9位旅行团的后代。 很多旅行团成员都不曾和子女提起过这段往事,比如杨式德和黄钰生。 其实,杨式德从出发起就每天记日记,深紫色的硬皮本,封面封底都没有字。在1976年去世时,这本日记和他保留下来的联大校徽、学生证、同学互赠的小照片,一起沉睡在他的书柜里。 黄珏生的女儿黄满,是在父亲去世十多年后,才发现父亲写过一份两万多字的自传。他就是那位旅行团的大管家,是大家都尊敬的人,是“管事得多,挨骂得也多”的黄院长。 旅行团经过坝陵桥  互联网似乎把一切都拉平了 这一趟走下来,我有一个特别直观的感受——互联网时代,好像一切都被拉平了。沿途的居民,似乎和你听着同样的歌,刷着同样的短视频,看着同样的电视剧。 但在其他层面,时间是不均质的。比如北上广的大面积拆迁似乎已经是历史,但在很多地方,它还是进行时,如果你再往里面走,它甚至还没开始。道理上明白是一回事,亲眼看到却是另一回事。 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生活久了,会经常忘记。 从盘县到富源的路上:胜境坊  新晃:县城一景  从楠木铺到马底驿:五里山附近,淌水过河的村民  你在大城市的路旁拦下一个人,会很不好意思,因为每个人都行色匆匆,好像每个人都奔着一个目的,需要做一件什么事儿,时间也很宝贵。 在小地方,你跟人聊天,人家就会给你搬一个板凳让你坐下来,甚至请你吃饭。 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,我叫他“江哥” 我在青溪认识了一个人,我叫他“江哥”。我当时只是向他问路,他便热情地请我回头吃饭,我随口答应,却没想到他后来找了十几里地专门接了我去他家。他说在我眼里没有看到设防的东西,这很少见。 在路上,我似乎触碰到了已经在中国城市里消失的“附近”,或者说,一种亲密的人情社会。 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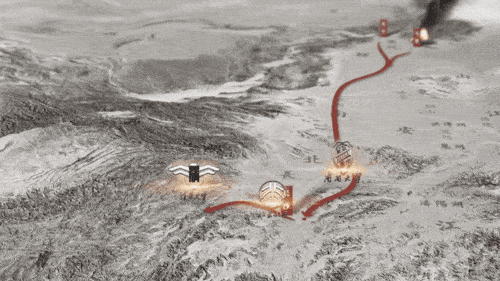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, 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 1938年4月28日,旅行最后一天。终于抵达大板桥时,黄钰生给大家带来新的袜子和精制麻草鞋。 年轻人“面孔是一样的焦黑,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。身上斜挂着油纸伞及水壶、干粮袋。”大家唱着“it’s a long way to 联合大学”。 一路走来,闻一多没生病没吃药,反而“满面红光能吃能睡,走起路来,举步如飞”。 而我是在2018年5月17日,到达的昆明金马碧鸡坊,买了支圆筒冰淇凌作为小小犒劳。 我后来才意识到,师生们从平津到长沙再到昆明,这中间有着官能与心灵的大变化,发生在抗战初年的此种变化最终影响了中国的未来。 梁思成、林徽因,在做古代建筑研究调查,他们也在路上;丰子恺在浙大任教,向贵州逃命,也在路上;沈从文、巴金、茅盾、老舍、萧乾也在路上。 这条路不只是一条现实的路,它还是一条历史叠成的路。这些人和故事一层层叠加起来,才构成了一个叫中国的东西。 部分图片由杨潇、杨嘉实、徐蓓提供,鸣谢《西南联大》纪录片片方 题图来源: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剧照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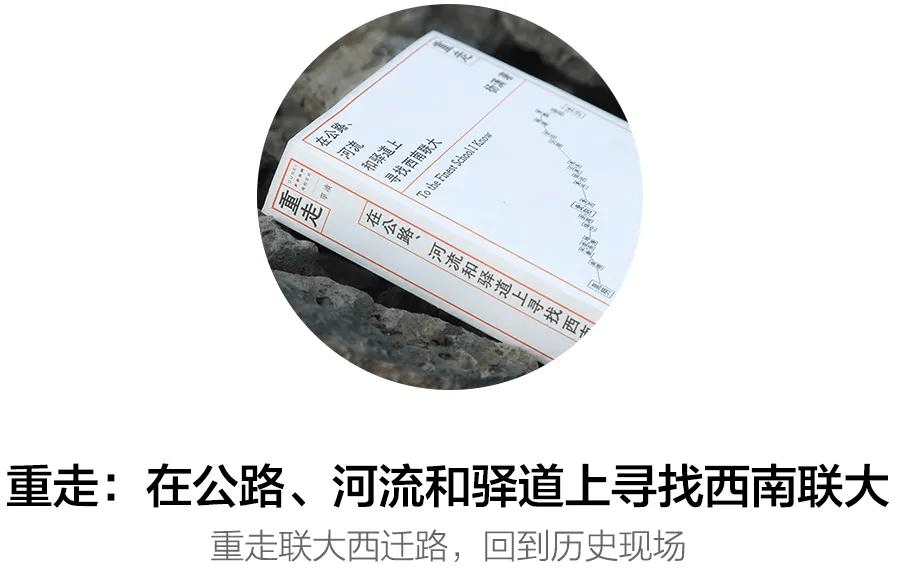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