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huozm32831 | 2025-09-25 20:19 |
|
《——【·前言·】——》 幽州二十年,父囚子、兄弑弟、民困政崩,宫殿华丽如宫阙,街巷却血迹未干。 刘守光自立为帝,三年应天,却迎来满城火光。一个藩镇政权,如何变成史书中的“桀燕”?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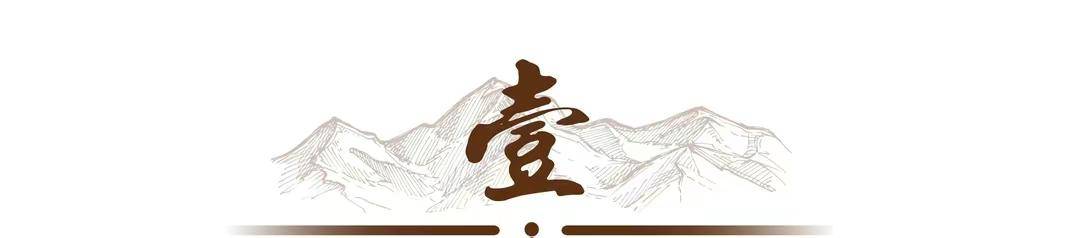 兴起与割据 唐末,河北幽州一带风雨飘摇。藩镇割据成风,权力交错不定。刘仁恭起于卢龙节度使之职,原为李克用部下,却逐渐自成气候。卢龙地带南通大道,北接边塞,是军事与商旅要道。仁恭掌握军队、财政,开始独立运作。幽州治下的地方势力渐被吸纳,他的控制力加深。  战争频仍。卷入唐末藩镇之间的混战,仁恭与邻镇交战,也与契丹边患斗争。秋天霜降之后,经摘星岭一带路线,仁恭曾命将焚烧关外野草,以削弱契丹骑兵之资。 草枯马少,契丹不得不折返或用重价赂买粮草。此种边防非常手段与非常态持续应用,使周边敌人畏惧。民众生活因此痛苦。征兵与征粮不断。税役重压。深州、乐寿等地田地连年荒废。人民逃难。 与此同时,仁恭姿态傲岸。他在幽州修建馆宇,模仿宫室。汇集术士道士讲长生羽化之道,图虚无之术。妾室艳妇被召入,宫中生活豪奢。礼仪仪轨渐近王者。  钱币名目增多,部下被指令用瑾泥等物制造钱币流通。财政制度被扭曲,社会秩序被妆点之奢糜所侵蚀。人口与财物被动员用于建设与宫室饰物。农民负担日重。 当时契丹侵扰边境频繁,民田被烧,村庄被掠,流民满州。仁恭父子不得不以兵防为务。民众既要承担兵役,也要承担役使与粮食供给。 家破人亡、流离失所的景象常见于边缘州县。州县官吏统治粗暴,审判不公,刑罚酷烈。 这些年间,权力不断集中于刘仁恭与其子刘守光。守光年少但手握重兵,他在父亲掌政之初就负责镇守边疆与调动军队。仁恭外征之余,守光留守幽州内部,掌握实权。  守光训练军队,整顿边防,扩大控制范围。他逐渐得到地方士族与基层将领的支持,同时也积累财富与兵权。 幽州的行政结构被修订。守光掌握户籍、税收与调兵选将之权。仁恭虽为节度使,却日渐依赖守光运行地方军事与行政。这样父子间权力分层日趋明确。 内政与军事由守光主理,仁恭则偏重外部形象与礼仪包裹。民众在守光管辖区中感受更深压迫:兵粮征调频次加倍,刑罚审官严厉,逃亡者难以追捕。 割据之局持续。中央唐廷对幽州管控力微弱。摧毁黄巾、剿灭其他割据势力虽为中央重任,但幽州地带的地形、交通、边患提供壁垒。  仁恭父子善用这一局面,他们既与邻镇结盟亦时有冲突。幕间变数多。守光时有出兵应战契丹。仁恭亦偶有出使或献贡,以保边界不被完全侵蚀。他们的割据既带有防御性质,又逐步变为近乎自立的政体。 人口流动荒废田地显著。农耕中断,村社瓦解。逃避兵役与重税的民众隐匿山中或迁往他地。地方志中“燕人逃亡”“田地被弃”的记录频见。赈荒稀少,灾年更是痛苦。 割据达二十年之久。仁恭在位期间,守光掌政能力稳步增强。幽州政权由最初依附与周边藩镇、中央政权的边缘状态,变为能自立称帝之势。内部财政、兵力、官僚体系渐趋完整。宫室礼仪模仿王朝标准。民间苦难与苛政并行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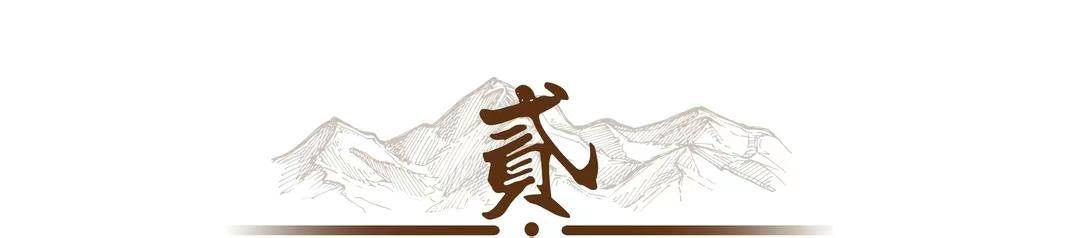 刘守光称帝与内部裂变 守光掌权后变数加剧。原本是父亲的军事副手与边防将领,操控实兵实权。他开始试探父权下的界限。对内,彼得利于地方士族与将领支持;对外,他观察中央政权之衰弱与藩镇间的争斗。父亲刘仁恭继续在幽州名义执政,守光则在实务中承担征兵、调度军械、官员任免,渐成实际主政者。 908年之时,守光权力积聚至可以与父挑战。他控制军队出入边境,常与契丹有接触或冲突。民间与军中多有言守光强于父、为政严苛之语。守光调度粮草与兵员频繁,国内平民负担加重,户部与赋税官吏多由守光直接指挥。  911年,守光称帝为燕主,改元“应天”。幽州旗帜更换,仪仗更加庄严。宫中礼制更向皇宫看齐。称帝之举之前,他已自行铸刀立法,严刑峻法。称帝之后更加明显。用刑之重、囚囹之苦、徭役之频,都超出仁恭时期。天子之名义被用来推行征税与役使。 内部裂变恐怖渐显。守光对兄弟无情。刘守文、刘守奇等被视为潜在威胁者。守光采取软禁、监视与威慑。兄弟之间地盘被削弱,兵权被收回。亲属中不忠者受到疑忌与惩罚。臣子若表现不服从或策略与守光意见相左者,多被撤职或更严重者斩首。  守光政权庆典与奢侈迅速铺开。兴建宫殿、修饰馆宇。妃嫔被召入宫。宫闱之中男女聚集。礼仪华丽,宴饮奢盛。与中央王朝相仿的仪仗仿佛宣称自己皇者之位的合法性。财政开支由此翻增。民间称税项、役使、贡物数量甚多。地方金融与摘星岭地区有关的财政负担尤为沉重。 守光称帝后,防御契丹成为重大问题。边疆战事频仍,契丹侵入次数增多。守光调遣军队、筑墙防线、烧田草、修置边堡,但因征税与徭役耗费,民生更加凋敝。逃民增加,经济生产驳营艰难。部分州县荒芜。工匠与农户逃往他地。  称帝与内部裂变相互推动。守光以称帝为中心展开统治形式改革,但这些改革加剧了内部矛盾。兄弟之间争斗,将领之间猜忌,地方士族与百姓之间怨怼。守光既要维护帝号的尊严,又要镇压异己、稳固权力。镇压手段多人记录:严刑、酷使、软禁、暗杀。家族血脉关系无法阻止被视为威胁者被削权或除去。 内部财政困难的情况被迫透出裂痕。宫室豪华者虽多,但军队供应与边防应付契丹侵扰时捉襟见肘。守光对内者以奢仪取信于贵族,对外者以战事维系权威。民间负担累累,民声四起。地方州县间纷纷逃役,实权地方将领时有倒向守光反对派或契丹使者求援者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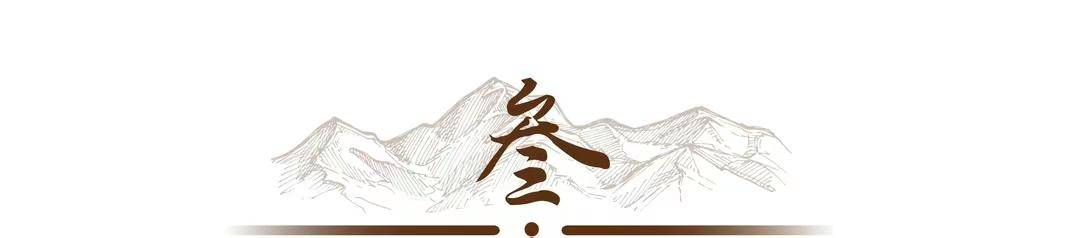 覆灭与灭亡过程 桀燕国终于走到尽头。应天三年(913年)秋末,形势急转而下。晋王李存勖发兵进幽州,目标直指燕都。李存勖集结晋军数万,自北方南下,呼应幽州边防将领。燕国边境抵抗虽然有些许回应,却因内部将领离心,叛变者渐多。边镇守将率队被诱而降,城防轻弱之处被迅速突破。 幽州城中城墙年久摇晃,水源粮草两耗。百姓逃散,城中士兵疲惫无战心。守光感到紧迫。逃亡与恐慌交错。幽州所在州县官吏报告粮食无以为继,民力耗尽。地震(或饥荒、盗匪)之类小规模灾害加重了本已疲敝的民生。守光尝试调兵应战,却不及晋军调度之灵活。晋军南下数线压境,多路合围。  幽州陷落当天夜里,守光惊知城中门户被攻破,守军误判晋军行径,城门被从内开。李存勖大军冲入,城中一片恐慌,守士纷纷弃城。守光携带小部近卫去城外,希望突围未果。晋军沿城南一路攻进宫城,守光出逃路线被截。他身边少数随从被杀。守光本人被捕。 叛变将领与投诚者蜂起。幽州城破之后,晋军士卒在城内搜捕守燕者。宫廷馆宇被洗劫,官吏被拘捕审问,重罪者斩首。燕国的大臣多为旧将和亲信,受到极刑者不少。 李存勖在幽州设立军事法庭,对守光朝中重臣严审。许多人被论以谋反罪、贪暴罪、虐民罪被处以死刑或囚禁。  守光被捉之后,幽州政权瓦解。国家机器停止运作。年号应天被废止。晋军宣布幽州归附。守光自身最后被处以极刑。幽州内外民众闻讯震动。 燕国灭亡之日,守光或被押至晋地,或在城破现场就地处死。至此,自刘仁恭开创幽州割据起,历十八年或二十年之久的燕政权彻底崩溃。  史书残影与“桀燕”之名 “桀燕”之称,无一史书自称,仅后世贬称。史书对刘守光统治之残暴有记载,但多为简略条目中官吏史家之评语,而非戏剧化情节。史书中“滥暴”“不仁”“酷用刑法”“民困”等语频见。残暴具体案例如守光称帝前后镇压异己者、兄弟被杀、父亲被囚。史书清楚指出守光囚禁父亲刘仁恭,自擒兄弟刘守文以巩固政权。 称帝之际,守光立国号大燕,改元应天。应天元年至应天三年。年号转换标志政权自立。史家评论数量暴政有所增加。条例粗暴。刑法严苛。官吏行使公权无制约。民间逃亡之情不绝于史。  “桀燕”这一名字,史家用以贬义之意昭示其不义。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》用“桀”之字,比其治下暴虐犹如商桀、殷纣之列。史书中并无“比朱温更残暴”的直接言辞,但后世文章、评论中有以朱温为标杆,将守光比作朱温的修辞。正史称朱温掌握梁朝、手腕狠辣,但守光之事迹被史官视为“不义之极”,常被列入暴政案例。 灭亡之后,守光及其父刘仁恭被杀。国号废除,疆域被晋所收回。幽州、蓟州、檀州、顺州等地恢复晋朝节度使或邻镇控制。权力归于李存勖。  “桀燕”暴政与残酷成为后世判断其政权合法性的核心。残暴被记录,不因修辞夸张,而因实事文献中见有血与刑、亲族反目、民众逃离、荒田弃作、边防失守这些事实。朱温与其比较,只是后世评论者为显对比所用。 |
|